译文及注释
译文
跋涉在道路崎岖又遥远的三巴路上,客居在万里之外的危险地方。
乱山上残雪在黑夜里闪光,一支烛火陪伴着我这异乡的人。
因离亲人越来越远,反而与书童和仆人渐渐亲近。
真难以忍受在漂泊中度过除夕夜,到明天岁月更新就是新的一年。
注释
迢递:遥远貌。三巴:指巴郡、巴东、巴西,在今四川东部。
羁危:在艰险中羁旅漂泊。
“烛”:一作“独”。人:一作“春”。
转于:反与。僮仆:随行小奴。
飘:一作“漂”。
明日:指新年。岁华:岁月,年华。
参考资料:
赏析
此诗写除夕之夜旅居之感怀。崔涂曾长期流落于湘、蜀一带,此诗为诗人客居四川时所作。此诗抒写诗人避乱流离巴蜀,旅途之中适逢除夕之夜的惨淡心情。全诗核心是一个“悲”字。首联即对,起句点地,次句点人,气象阔大;颔联写除夕客居异地的孤独;颈联写亲眷远离,僮仆成了至亲,再烘托“独”字;尾联点出时逢除夕,更不堪漂泊。全诗流露出浓烈的离愁乡思和对羁旅的厌倦情绪。
“迢递三巴路,羁危万里身”,写离乡的遥远和旅途的艰辛:感叹三巴道路的迢远,感叹与故乡的万里相隔。诗人只身流离万里之外,举目无可亲之人,生活的艰辛,生命的危险,如影随形地纠缠着他。“迢递”“羁危”用字精炼而准确,让人顿感起笔之突兀。同时,“三巴路”“万里身”又显得气象宏大,真可谓“蜀道之难难于上青天”,生动地反映出巴蜀的山川形势。虽是深挚地抒发飘泊天涯的无限情怀,却并不给人以萧瑟的感觉。
“乱山残雪夜,孤烛异乡春”,具体地描绘出了异乡除夜的凄凉。住所外面,是覆盖着残雪的乱山;屋里,孤零零的一支蜡烛陪伴着诗人。“乱山”、“残雪”既是写旅居的环境,也是在烘托诗人除夕之夜的纷乱、凄凉的心清。写山用一“乱”字,展现其杂乱的形态,借以写诗人诸事纷杂的心态;写雪用一“残”字,既扣住了时令,又写出残冬余寒未消,借以表现心境的凄冷。此二字皆诗人匠心运筹、刻意锤炼的笔墨。“孤烛”二字也具有很强的表现力,往年过除夕,合家团聚,虽说生逢乱世,节日清贫,总还是快慰的;如今过除夕,却是独自一人处在异乡,论相伴者,只有无言的蜡烛,而蜡烛又是孤独一支,“孤烛”照孤客,孤客对“孤烛”,物态人情,相互映衬,有力地揭示出诗人孤苦的心境。此句与马戴的《灞上秋居》“落叶他乡树,寒灯独夜人”一句,可谓是异曲同工,同样扣人心弦,读来令人心碎。
“渐与骨肉远,转于僮仆亲”,真切地写出了久别家乡之人常有的亲疏情感。文字虽直朴,道情却非常细腻曲折。在家时,有骨肉相伴,自然感觉不到僮仆的可亲之处;如今飘泊在外,远离了亲人,与骨肉远隔,无法与亲人们一同迎接新年,故而对于身边朝夕相处的僮仆才倍感亲近,同时也为除夕增添了一些欢乐。对僮仆感情的转变,固然是好事,但这也暗中陈述诗人当时处境的寂寞孤独和生活的拮据困窘。诗人用笔巧妙,明写“情亲”之乐,暗道羁旅之苦,于无字之处发出一片浩叹。此联语言质朴,感情细腻,与第二联互相映衬,真挚感人。
“那堪正飘泊,明日岁华新”,归结本题意旨,言不堪在这飘泊的生涯里过此除夕,想到明日又增一岁不禁愁苦万分。所以,诗人寄希望于新年,祈祷不再漂泊流离,显得顺理成章,真切自然。这种结尾统摄了全篇的情感,把叹羁旅、思故乡、念骨肉、感孤独诸多纷杂的心绪归为“那堪”二字,以强化之,又用“明日岁华新”把这些思绪框定在“除夜”,意境鲜明,结构严谨。句中的“明日”紧扣题中的“除夜”二字,于篇末点题,强烈地表达了诗人不堪忍受的异乡飘泊,希望早日结束羁旅生涯的愿望。离愁乡思,发泄无余。
全诗语言朴素,铅华皆无,于平实之处涌动真情,意境苍凉,语言工丽,感情真挚,刻画细腻,情韵幽绝,感人至深。“乱山”一联堪称佳句,令人回味无穷。
崔《除夜有感》:“迢递三巴路,羁危万里身。乱山残雪夜,孤烛异乡春。渐与骨肉远,转于僮仆亲。那堪正漂泊,明日岁华新?”读之如凉雨凄风飒然而至,此所谓真诗,正不得以晚唐概薄之。按崔此诗尚胜戴叔伦作。戴之“一年将尽夜,万里未归人。寥落悲前事,支离笑此身,”已自惨然,此尤觉刻肌砭骨。崔长短律皆以一气斡旋,有若口谈,真得张水部之深者。如“并闻寒雨多因夜,不得乡书又到秋”、“正逢摇落仍须别,不待登临已合悲”,皆本色语佳者。至《春夕》一篇,又不待言。
参考资料:
崔涂 [唐] (约公元八八七年前后在世),字礼山,善音律,尤善长笛,《唐才子传》说是江南人,一九七八年版人民文学出版社《唐诗选》以其[旧业临秋水,何人在钓矶]及[试向富春江畔过,故园犹合有池台]句,推为今浙江桐庐、建德一带人。唐末诗人,生卒年、生平均不详,约公元八八八年前后在世。唐僖宗光启四年(888)进士,壮客巴蜀,老游龙山,故也多写旅愁之作。其《春夕旅怀》[胡蝶梦中家万里,杜鹃枝上月三更],颇为传诵。《全唐诗》存其诗1卷。他写的最有名的一首诗是《除夜有怀》。
凤求凰琴慢弹,莺求友曲休咀,楚阳台更隔着连云栈,桃源洞在蜀道难。
【搅筝琶】无边岸,黑海也似那煎烦。愁万结柔肠,泪双垂业眼。泪眼与愁肠,直熬得烛灭香残。更阑,望情人必然来梦间,争奈这枕冷衾寒。。
【落梅风】粘金雁,亸翠鬟,想不曾做心儿打扮。近新来为咱情绪懒。不梳妆也自然好看。
【沉醉东风】风铃响猛猜做佩环,柳烟颦只疑是眉攒。想犀梳似新月牙,忆宫额似芙蓉瓣,见桃花呵似见他容颜,觑得越女吴姬匹似闲,厌听那银筝象板。
【本调煞】相思成病何时慢,更拚得不茶不饭,直熬个海枯石烂。
世人作梅词,下笔便俗。予试作一篇,乃知前言不妄耳。
藤床纸帐朝眠起,说不尽无佳思。沉香断续玉炉寒,伴我情怀如水。笛声三弄,梅心惊破,多少春情意。
小风疏雨萧萧地,又催下千行泪。吹箫人去玉楼空,肠断与谁同倚。一枝折得,人间天上,没个人堪寄。
 崔涂
崔涂 乔吉
乔吉 朱敦儒
朱敦儒 蔡伸
蔡伸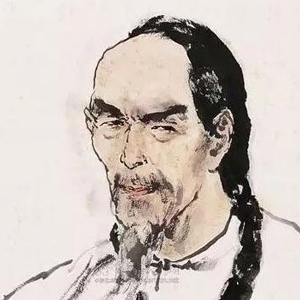 龚自珍
龚自珍 纳兰性德
纳兰性德 周邦彦
周邦彦 柳永
柳永 李清照
李清照 辛弃疾
辛弃疾