译文及注释
译文
禹、汤和周文王以文德治国的美德已经越来越淡薄,随之实行残酷的肉刑。
太仓令(淳于意)被诬有罪,押解到长安城。
只悔恨没生儿子,困苦危难时才孤立无援。
小女(淳于缇萦)听父亲这么说心痛不已,她想人死了哪还能复生。
她到皇宫门前给汉文帝上书,并在宫门前吟唱《鸡鸣》诗。
缇萦号哭阙下、伤心断肠,而见不到君王更忧心如焚。
圣明的孝文帝,终于被至诚所感动。
天下男儿为什么那么愚笨无能,竞比不上弱女子缇萦。
注释
三王:当指夏商周三代的开国君主禹、汤和周文王。德:文德。弥:副词,益,越来越。薄:衰减,淡薄。传说三代圣王以文德治天下,故“刑错而兵寝”(刑罚不用,兵器也收藏起来)。其后则文德日渐衰微,各种各样的刑罚也就多起来。
惟:语气词。肉刑:古时切断肢体、割裂肌肤的刑罚,包括墨刑、劓(yì)刑、剕(fèi)刑、宫刑、大辟等。
太仓令:官名,管理太仓(汉代政府储粮之仓)的行政长官。缇萦之父淳于意曾担任齐之太仓令。
就递:递解。“递”,《文选》作“逮”。
身:自身,自己。
困急:危急关头。
茕(qióng)茕:孤独之状。汉文帝四年(前175),有人告发太仓史淳于意触犯刑律。淳于意被逮,押赴长安。淳于无子,有五女。将行,“骂其女曰:生子不生男,有缓急,非有益也。’”(史记·孝文纪》)
诣(yì):到。阙(què)下:阙谓宫阙,阙下代指朝廷。“小女”以下三句,言缇萦向皇帝上书,自请为官婢以续父亲之刑。《史记》载:“其少女缇萦自伤泣,乃随其父至长安,上书曰:“臣父为吏齐中,皆称其廉平。今坐法当刑。妾伤夫死者不可复生,刑者不可复属。虽复欲改过自新,其道无由也。妾愿没入为官婢,赎父刑罪,使得自新。”
鸡鸣:《诗经·齐风·鸡鸣》。全诗以对话形式写女子催促丈夫上朝,是“鸡鸣戒旦”成语的出处。据《文选》注引刘向《列女传》,缇萦伏阙上书之时,尝歌《鸡鸣》《晨风》之诗。按《鸡鸣》中有“匪鸡则鸣,苍蝇之声”、“匪东方则明,月出之光”之语,缇萦歌咏此诗,似在表明父亲所获之罪与事实不符。
摧折裂:谓断裂。此句形容缇萦号哭阙下、伤心断肠之状。
晨风:《诗经·秦风·晨风》。《诗序》谓此诗乃刺国君弃其贤臣之作。后人多以为歌咏女子“未见君子”之忧。
圣:圣明。孝文帝:汉文帝刘恒,汉高祖刘邦之子,公元前179年至前156年在位。在位期间提倡农耕、轻徭薄赋,国富民强,与其子汉景帝统治时代并成为“文景之治”。
恻然:悲悯之状。至情:至真至纯之情。此二句言缇索之举感动文帝,下诏免其父之罪并废止肉刑。《史记》云:“天子怜悲其意,乃下诏今人有过,教未施而刑加焉。或欲改行为善而道无由也。朕甚怜之。夫刑,至断支(肢)体,刻肌肤,终身不息,何其楚痛而不德也,岂称为民父母之意哉?其除肉刑。”
愦(kuì)愦:昏愚。▲
创作背景
东汉永元元年(89),大将军窦宪伐匈奴,征班固为中护军。后窦宪败,班固坐免官,又因为诸子不尊法度、得罪洛阳令种竞而被捕,于永元四年(92)卒于狱中。这首诗大约是班固晚年在狱中所作。
赏析
该诗借用西汉文帝时缇萦上书的事迹,表达了对诸子不肖使自己受到牵累的哀伤与无奈, 同时也流露出能够因圣主明君发动恻隐之心而获得宽宥的微茫期许。该诗叙事凝练,语言质朴;全诗中遣字用韵融入声韵理论,偶句押韵,一韵到底,全押平声。该用韵方式为后人写古诗效法,也接近唐律诗用韵方式。
全诗可分为三部分。开首两句,是第一部分。简短捷说。追叙肉刑起始,以引出太仓令将受肉刑一事。这两句,类似全诗的“引子”,却暗含着对肉刑的谴责。意思是说,夏禹、商汤、周文王等三王的仁德之治,随着时代的变迁,渐渐被淡薄了,后来就使用起了肉刑。赞“三王”之道用“德”,那么“用肉刑”者自是不德。作者对残暴肉刑的谴责,对仁德之政的向往,就尽在这两句中了。
由“太仓令有罪”至“恻然感至情”,是第二部分。这部分是叙述缇萦之父获罪,缇萦上书救父,汉文帝深受感动的历史故事。
在这部分中,诗人先用四句,来写齐太仓令淳于意获罪,将被递解长安受刑,以及他自恨没有男儿,到危急之时深感孤独无援的悲痛。再用四句,来写幼女缇萦伤于父亲“生子不生男,缓急无可使者(指危急时无可用之人)”的话,伤于父亲的命运,想到古歌《鸡鸣》中那“虫来啮桃根,李树代桃僵”的诗句,于是随父至京,“诣阙下(即到宫阙之下)”上书朝廷,“愿入身为官婢,以赎父刑罪”。接下来两句“忧心摧折裂,晨风扬激声”,是渲染缇萦的为父心忧和上书之言,足以使天地折裂,晨风为之传颂。其悲壮之言行,足以感天动地。果然,连皇帝也被感动了。这两部分的末两句,“圣汉孝文帝,侧然感至情”,就是写汉文帝被他那孝父至情所感动,顿生恻隐怜悯之情。结果是不言而喻的,正如《史记·扁鹊仓公列传》所载,“上悲其意,此岁中亦除肉刑法。”
缇萦,身为一个封建社会的弱女子,竟敢伏阙上书,甘愿没身为婢以赎父罪,并且希望废止肉刑而给人以改过自新的机会。其情可悯,其见甚明,其行亦悲壮矣。
因而,诗人在最后一部分,用两句,将她的言行与男子作比道:“百男何愦愦,不如一缇萦!”以“百男”与一女作比,本身已见出高下之势:百男竟“不如”一女,则更见出此女子的不同凡俗。作者正是通过这样一个强比,将他对这奇女子的敬佩和盛赞之情,以及对“百男”的轻蔑之意,充分地表达出来了。
该诗有两点需要说及。一是,在男尊女卑的封建社会,班固能以“百男何愦愦,不如一缇萦”的态度,来歌颂一个奇女子,已属难能可贵。二是,此诗虽仅老实叙事,缺乏文采和形象性,但它毕竟是有文献可考的第一首文人五言诗,那种初学者的质朴和幼稚是情有可原的,而作者那种敢于实践新诗体的精神,也是可贵的。▲
班固(32年—92年),字孟坚,扶风安陵(今陕西咸阳东北)人,东汉著名史学家、文学家。班固出身儒学世家,其父班彪、伯父班嗣,皆为当时著名学者。班固一生著述颇丰。作为史学家,《汉书》是继《史记》之后中国古代又一部重要史书,“前四史”之一;作为辞赋家,班固是“汉赋四大家”之一,《两都赋》开创了京都赋的范例,列入《文选》第一篇;同时,班固还是经学理论家,他编辑撰成的《白虎通义》,集当时经学之大成,使谶纬神学理论化、法典化。
杨柳岸秋千高架,梨花院仕女双丫,玉纤轻按小琵琶。花明春富贵,响玉
交加,东风人信马。 山居
蕨薇嫩山林趣味,桑麻富田野生涯,市喧声不到衡扉。绿香春酒瓮,红润晓
花枝,日高眠未起。 春醉
红叱拨轻总宝,紫葡萄满泛金钟,寻芳人在小帘栊。倚风同笑傲,对月唱
玲珑,清闲可意种。 忆西湖
花院小低低朱户,酒旗摇簇簇香车,市桥官柳暗西湖。杯浮金潋滟,寺现玉
浮图,莺花谁是主? 自况
万顷烟霞归路,一川花草香车,利名场上我情疏。蓝田堪种玉,鲁酒可操觚,
东风供睡足。
 班固
班固 吴西逸
吴西逸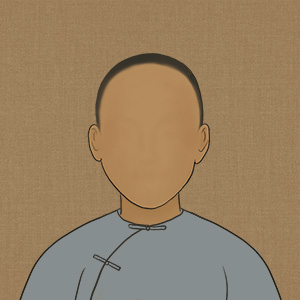 张良臣
张良臣 元好问
元好问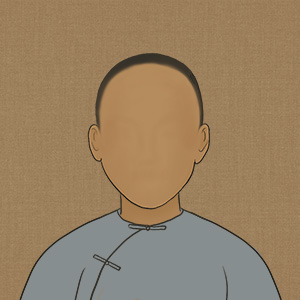 王国维
王国维 张孝祥
张孝祥 王士祯
王士祯 纳兰性德
纳兰性德 温庭筠
温庭筠 苏轼
苏轼