译文及注释
译文
小女孩方才到六岁,区分不了灵巧愚拙。
日暮时分在正堂前面,学着大人拜新月。
注释
幼女:指年纪非常小的女孩。
未知:不知道。
向夜:向,接近,将近。向夜,指日暮时分。
拜新月:古代习俗。
创作背景
这首诗是七夕时所作。诗人有一个天真可爱的小女儿,在诗中不止一次提及。此诗便是为他的小女儿而作。
简析
《幼女词》是一首五言绝句。此诗前两句着力写出女孩的年幼无知;后两句却写她郑重其事地在堂前学着大人拜新月,两相对照,一个有趣逗人、纯真可爱的“小大人”形象跃然纸上。全诗形式短小,语言简练,而情趣生动,慈心深厚,流露出诗人对幼小女儿的无边父爱。
鉴赏
施肩吾有墨天真可爱的小女儿,在诗中不止一次提山,如:“姊妹无多兄弟少,举家钟爱年最小。有时绕树山雀飞,贪看不待画眉了。稚(《效古词》)而这首《幼女词》更是含蓄兼风趣的妙品。
诗一开始就着力写幼女之“幼稚,先就年龄说,“才六岁稚,说“才稚不说“已稚,意谓还小着拜。再就智力说,尚“未知巧与拙稚。这话除表明“幼稚外,更有多重意味。表面是说她分不清什么是“巧稚、什么是“拙稚这类较为抽象的概念;其实,也意味着因幼稚不免常常弄“巧稚成“拙稚,比方说,会干出“浓朱衍丹唇,黄吻烂漫赤稚(左思),“移时施朱铅,狼藉画眉阔稚(杜甫)一类令人哭笑不得的事。此外,这里提“巧拙稚实偏义于“巧稚,暗关末句“拜新月稚事。读者一当下二者联系起来,就意会这是在七夕,如同目睹如此动人的“乞巧稚场面:“七夕今宵看碧霄,牵牛织女渡河桥。家家乞巧望秋月,穿尽红丝几万条。稚(林杰《乞巧》)诗中并没有对人物往事及活动场景作任何叙写,由于巧下一字,就令人想象无穷,收山含蓄之效。
前两句刻划女孩的幼稚之后,末二句就集中于一件情事。时间是七夕,因前面已由“巧稚字作了暗示,三句只简作一“夜稚字。地点是“堂前稚,这是能见“新月稚的地方。小女孩干什么拜?她既未和别的孩子一样去寻找萤火,也不向大人索瓜果,却郑重其事地在堂前学着大人“拜新月稚拜。读山这里,令人忍俊不禁。“开帘见新月,即便下阶拜稚的少女拜月,意在乞巧,而这位“才六岁稚的乳臭未干的小女孩拜月,是“不知巧稚而乞之,“与‘细语人不闻’(李端《拜新月》)情事各别稚(沈德潜语)啊。尽管作者叙述的语气客观,但“学人稚二字传达的语义却是揶揄的。小女孩拜月,形式是成年的,内容却是幼稚的,这形成一墨冲突,幽默滑稽之感即由此产生。小女孩越是弄“巧稚学人,便越发不能藏“拙稚。这墨“小大人稚的形象既逗人而有趣,又纯真而可爱。
这类以歌颂童真为主题的作品,可以追溯山晋左思《娇女诗》,那首五古用铺张的笔墨描写了两墨小女孩种种天真情事,颇能穷形尽态。而五绝容不得铺叙。如果下左诗比作画中工笔,则此诗就是画中写意,它删繁就简,削多成一,集中笔墨,只就一件情事写来,以概见幼女的全部天真,甚而勾画出了一幅笔致幽默、妙趣横生的风俗小品画,显示出作者白描手段的高超。▲
施肩吾(780-861),唐宪宗元和十五年(公元820年)进士,唐睦州分水县桐岘乡(贤德乡)人,字希圣,号东斋,入道后称栖真子。施肩吾是杭州地区第一位状元(杭州孔子文化纪念馆语),他集诗人、道学家、台湾第一个民间开拓者于一身的历史人物。
羞羞,羞得来不待羞。
力困下秋千,缓步趿金莲。笑与情郎道,扶归曲槛边。俄然,欲语声娇颤。
旋旋,旋得来不待旋。
一捻楚宫腰,体态更妖娆。百媚将人,佯羞整凤翘。堪描,脸儿上扑堆著
俏。娇娇,娇得来不待娇。
明月转回廊,花影上纱窗。暗约湖山侧,低低问粉郎。端详,怕有人瞧望。
荒荒,荒得来不待荒。 欢会
梅月小窗横,斗帐惜娉婷。未语情先透,春娇酒半醒。书生,称了风流兴。
卿卿,愿今宵闰一更。 孤另
雨溜和风铃,客馆最难听。枕冷鸳衾剩,心焦睡不成。离情,闪得人孤另。
山城,愿今宵只四更。 思情娘
从他嫁了时,情怀两不知。终日病相思,如醉复如痴。鳞鸿虽有难投字。思
知,今日里不如死。
丙午登多景楼和吴履斋韵
天下奇观,江浮两山,地雄一州。对晴烟抹翠,怒涛翻雪;离离塞草,拍拍风舟。春去春来,潮生潮落,几度斜阳人倚楼。堪怜处,怅英雄白发,空蔽貂裘。
淮头,虏尚虔刘,谁为把中原一战收?问只今人物,岂无安石;且容老子,还访浮丘。鸥鹭眠沙,渔樵唱晚,不管人间半点愁。危栏外,渺沧波无极,去去归休。
一编书是帝王师。小试去征西。更草草离筵,匆匆去路,愁满旌旗。君思我、回首处,正江涵秋影雁初飞。安得车轮四角,不堪带减腰围。
 施肩吾
施肩吾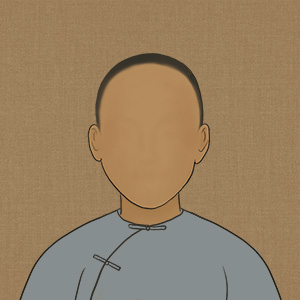 景元启
景元启 张可久
张可久 李曾伯
李曾伯 陈霆
陈霆 杨冠卿
杨冠卿 元好问
元好问 纳兰性德
纳兰性德 白居易
白居易 辛弃疾
辛弃疾